AG尊龙 AGzunlong 分类>>
梅AG尊龙凯时- 尊龙凯时官方网站- APP下载兰芳的“文人朋友圈”
尊龙凯时官网,尊龙凯时,AG尊龙凯时,尊龙娱乐,尊龙体育,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,尊龙凯时体育,尊龙凯时平台,ag尊龙,尊龙平台,尊龙,尊龙官网,尊龙登录入口,尊龙官方网站,尊龙app下载,尊龙凯时APP下载尊龙凯时官网,尊龙凯时,AG尊龙凯时,尊龙娱乐,尊龙体育,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,尊龙凯时体育,尊龙凯时平台,ag尊龙,尊龙平台,尊龙,尊龙官网,尊龙登录入口,尊龙官方网站,尊龙app下载,尊龙凯时APP下载尊龙凯时官网,尊龙凯时,AG尊龙凯时,尊龙娱乐,尊龙体育,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,尊龙凯时体育,尊龙凯时平台,ag尊龙,尊龙平台,尊龙,尊龙官网,尊龙登录入口,尊龙官方网站,尊龙app下载,尊龙凯时APP下载尊龙凯时官网,尊龙凯时,AG尊龙凯时,尊龙娱乐,尊龙体育,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,尊龙凯时体育,尊龙凯时平台,ag尊龙,尊龙平台,尊龙,尊龙官网,尊龙登录入口,尊龙官方网站,尊龙app下载,尊龙凯时APP下载尊龙凯时官网,尊龙凯时,AG尊龙凯时,尊龙娱乐,尊龙体育,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,尊龙凯时体育,尊龙凯时平台,ag尊龙,尊龙平台,尊龙,尊龙官网,尊龙登录入口,尊龙官方网站,尊龙app下载,尊龙凯时APP下载

齐如山出身书香门第,家学渊源深厚,又曾游历欧洲,观摩过欧洲戏剧。回国后他潜心钻研中国戏曲,成为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大家。他与梅兰芳的缘分始于一次偶然的观戏。20世纪初年,齐如山看过梅兰芳的戏,并未觉得惊艳。直到一次广德楼义务戏,唱倒三的梅兰芳因当天另有三处堂会戏,一时赶不过来,倒二的杨小楼先上台,观众却不买账,大喊退票。好在梅兰芳当天演的都是《樊江关》,不用卸妆,匆匆赶来直接上台才化解了观众的情绪。齐如山发现梅兰芳之所以有观众缘,在于“嗓音好”“会唱”“身材好”“身段好”“面貌好”“会表情”,这是成为名角得天独厚的条件,自此他开始帮助梅兰芳。1912年看完梅兰芳《汾河湾》后,觉得尚有精进空间,便提笔写了一封3000字长信,指点梅兰芳的身段、表情与水袖运用等。令齐如山意外的是,梅兰芳在下次演出中竟将这些建议一一呈现。自此,两人开启了多年的深度合作。
齐如山是梅兰芳编剧团队中的首席与核心。从针砭时弊的《牢狱鸳鸯》《一缕麻》,到充满古典意味的《嫦娥奔月》《黛玉葬花》《洛神》,这些经典剧目的构思、提纲、初稿乃至场次安排,都浸润着齐如山的心血。他与梅兰芳身边的文人群体一道,巧妙地将书画意境、诗词韵味以及古典舞蹈的精髓(如袖舞、羽舞等)融入表演,共同塑造了“梅派”独特的美学风格。齐如山兼具编剧、导演、策划等多重身份,在三四十年间,他走访了三四千位京剧界人士,著书立说,其中《中国剧之组织》《梅兰芳艺术之一斑》《梅兰芳游美记》等著作专为梅兰芳而作。为帮助梅兰芳访美,他前后准备了七八年时间,可谓苦心孤诣。齐如山不仅为梅兰芳创作大量新戏,助其走向世界,更在艺术理论上给予指导。他提出的“无声不歌,无动不舞”“不许写实”“不许真器物、真东西上台”等观点,准确概括了中国戏曲的本质特征。齐如山与梅兰芳的深度合作,堪称理论家助力艺术家的典范,他们共同探索京剧表演艺术规律,使梅派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度。
清末最后一位状元张謇,比梅兰芳大41岁,两人结为忘年交。1915年,梅兰芳的《嫦娥奔月》轰动京城,张謇自然成为“梅迷”。袁世凯复辟时,张謇愤然辞官,回到家乡南通兴办实业和教育,并花费巨资建造更俗剧场,创办伶工学社。伶工学社最初拟聘梅兰芳,因梅兰芳忙于出访日本,具有改革理想的欧阳予倩成为伶工学社主任,梅兰芳任名誉社长。1919年11月至1922年,梅兰芳在四年时间里三次到南通演出,张謇在更俗剧场专辟“梅欧阁”,并亲书匾额和对联,以表彰“南欧北梅”的艺术成就。张謇并非一般梅迷,而是不断启发、教育、提点梅兰芳。他还将得意门生李斐叔介绍给梅兰芳,李斐叔跟随梅兰芳近20年,其撰写的《梅兰芳游美日记》《梅边杂忆》等数十万字著述,成为梅兰芳研究的珍贵文献。
吴震修、李释戡、许伯明等人虽曾留学日本,但自幼入私塾,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。吴震修回国后成为梅党之首冯耿光的得力助手,他对梅兰芳,在生活上规范其行为,在经济上给予资助,在艺术上深度参与。1931年梅兰芳组织国剧学会,吴震修担任理事。对于《嫦娥奔月》的服装,吴震修认为“不宜太深,尤其不能在上面绣花,应该用素花和浅淡的颜色,才合嫦娥的性格”。《霸王别姬》最初由齐如山撰写初稿,原本两天演完,吴震修认为必须改成一天演完,并亲自删减不少场次,经大家润色加工后,该剧成为梅兰芳的代表作。李释戡在冯耿光的介绍下结识梅兰芳,后成为梅兰芳智囊团的核心成员,被称为“秘书长”“戏口袋”。李释戡教授梅兰芳诗词,并谆谆教诲他“为艺不可不读诗,戏中若多诗美,则戏能美,人亦自美”,激励他从古诗中汲取艺术养分。他参与编剧的《洛神》,将曹植《洛神赋》等内容巧妙融入戏中。《嫦娥奔月》《黛玉葬花》《千金一笑》《天女散花》等剧目,基本都是由齐如山拟定提纲,李释戡、罗瘿公、黄秋岳等人集体创作完成。李释戡取姜夔词“苔枝缀玉。有翠禽小小,枝上同宿”之句,自号书斋“唤玉簃”,并为梅兰芳的书斋取名“缀玉轩”。后来,“缀玉轩”成为梅兰芳读书、写字、绘画、会客的重要艺术空间。1923年李释戡作《梅兰芳小传》,其中提到“歌舞合一,有复古之功,群以‘梅派’尊之”,这是最早将梅兰芳艺术归纳为“梅派”的表述。曾就读于金陵同文馆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许伯明,在梅兰芳1913年上海演出时,就与冯耿光、李释戡等人一起为梅兰芳出谋划策。1919年梅兰芳首次访日,许伯明担任随团顾问。他还将堂弟许姬传、许源来介绍给梅兰芳,二人成为梅兰芳的得力助手,最大贡献是与梅合作撰写了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,该书经旁搜博采、考证辨订,成为可靠的口述史典范。
此外,康有为首席弟子罗瘿公、“寒庐七子”之一的诗人易顺鼎、“晚唐诗派”重要诗人樊樊山、“晚清四大家”之一的词人况周颐等人,都曾与梅兰芳有过密切交往。这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对梅兰芳的滋养,远不止于诗文褒扬、参与剧目创作或理论指导,更在于全方位提升了其为人、为艺的修养。他们与梅兰芳的深度合作,是文化转型期的一种特殊现象。身处时局动荡、内忧外患的时期,这些人将失落的文化理想寄托于戏曲艺术,既承续了文人参与戏曲创作的传统,也直接推动了京剧艺术的革新,为京剧注入了丰厚的文化内涵,使其逐渐从市井娱乐转变为高雅艺术。
提及胡适与梅兰芳的交往,齐如山曾回忆道:“在民国初年他常到舍下,且偶与梅兰芳同吃便饭,畅谈一切。”可见二人20世纪初便已熟识。1919年,胡适的导师约翰·杜威来华讲学,胡适不仅陪同其观看梅兰芳的演出,还亲自带他拜访了梅兰芳。此后多年,胡适始终是梅兰芳艺术事业的重要支持者。尤其在梅兰芳筹备访美演出期间,胡适倾力相助:他凭借自身在美国的影响力,为梅兰芳书写了多封介绍信,还将梅派名剧《太真外传》分别译成英文和日文,并撰写英文专文《梅兰芳和中国戏剧》向美国观众推介。此外,他还为演出剧目的选择提供了宝贵建议。无论是梅兰芳启程赴美时的送行队伍,还是他载誉归来的欢迎仪式,都能看到胡适的身影。1935年梅兰芳计划访苏演出时,胡适再次献策,建议由张彭春和余上沅分任剧团正、副导演,体现了他在艺术规划上的远见。
一位是梨园泰斗,一位是新派诗人,梅兰芳与徐志摩两人看似人生轨迹迥异,交集甚少。然而,现存文献中的记载,正逐渐勾勒出这段曾被忽略的深厚情谊。1923年,徐志摩因公开赞誉梅兰芳而开罪新剧界人士,引发了一场笔墨官司。次年(1924年)泰戈尔访华,担任其翻译的徐志摩与梅兰芳有了更密切的互动,5月8日,梅兰芳观看了徐志摩、林徽因等为泰戈尔祝寿排演的名剧《齐德拉》。5月19日,徐志摩又陪同泰戈尔专程欣赏了梅兰芳的《洛神》,泰戈尔还对布景提出了宝贵意见。此后,两人的交往持续深入。梅兰芳筹备赴美演出前后,都曾专程拜访徐志摩。法国国家歌剧院秘书长赖鲁雅来华考察中国戏剧音乐时,徐志摩与梅兰芳更是频繁接触,共同为中法戏剧交流做出了贡献。令人遗憾的是,徐志摩生前曾允诺为梅兰芳创作剧本,可惜因其意外早逝未能如愿。梅兰芳为徐志摩写下挽联:“归神于九霄之间,直看噫籁成诗,更忆拈花微笑貌;北来无三日不见,已诺为余编剧,谁怜推枕失声时。”字里行间,满是对挚友早逝的无尽哀思与未竟合作的深深痛惜。
抗战期间,梅兰芳蓄须明志,坚决拒绝为日伪政权演出,彰显了崇高的民族气节。1949年初,地下组织委派夏衍、熊佛西动员梅兰芳留在上海,他欣然应允。上海于1949年5月27日解放,梅兰芳自5月31日起为将士连续演出三场。首场演出刚一落幕,陈毅市长便在夏衍的陪同下,前往后台看望梅兰芳。10月1日,梅兰芳在城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。新中国成立后,梅兰芳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与指导下,积极著书立说,并开启全国巡演,致力于将艺术奉献给广大人民群众。在这一过程中,他与田汉、郭沫若、张庚等文艺界人士建立了紧密联系。
梅兰芳与田汉初识是在1922至1923年上海的某次宴会上,当时在座的还有吴昌硕、郭沫若等人。两人交往更为密集的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前后,其间一同参加了第一届文代会、戏曲改进委员会、政协一届一次会议等多项活动。1951年,田汉担任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,梅兰芳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。1953年,二人又分别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与副主席,在文艺事业中形成了紧密的协作关系。1956年12月,在田汉的帮助和推动下,梅兰芳赴毛主席故乡演出20余天。1958年10月至11月,田汉与梅兰芳分任正副团长的“文艺界福建前线慰问团”,在福州、厦门等地累计演出78次,田汉后来在《追悼梅兰芳》中特别提到,梅兰芳“冒着敌人炮火的危险在战壕中清唱”,高度赞扬其奉献精神。1959年,梅兰芳演出《穆桂英挂帅》后,田汉评价该剧“沉雄慷慨”,并亲自修改了主要唱词。1961年8月8日梅兰芳逝世后,田汉于9月10日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梅兰芳纪事诗(二十五首)》,其中“鲁迅忧疑岂偶然?半描官阃半神仙。终能打破玻璃罩,国恨家仇入管弦”一首,既肯定了梅兰芳的民族大义,也点明了其艺术服务对象的深刻转变。
郭沫若在与梅兰芳的交往中,曾多次表达对其艺术与人格的推崇。1946年,他在写给梅兰芳的书法作品中曾言:“俄国人民仅知中国有二人,一为孔夫子,一则梅博士也”,以此称颂梅兰芳的艺术水准与国际影响力。1956年,郭沫若与梅兰芳同老舍、巴金、田汉、钱学森、华罗庚等人共同参加了堪称“中国第一届春晚”的“春节大联欢”,梅兰芳在此次活动中演出了他的拿手戏《宇宙锋》。1961年5月31日,梅兰芳在中国科学院礼堂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演出——《穆桂英挂帅》,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排演的唯一一出新戏。演出结束后,他与郭沫若亲密合影。梅兰芳逝世后,郭沫若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在梅兰芳长眠榻畔的一刹那》,深切回忆这次演出:“使那小小的礼堂成为了无限大的宇宙”,以此定格这场充满光辉的艺术绝唱。1962年,阿英编剧的传记纪录片《梅兰芳》在梅兰芳逝世一周年之际拍摄完成。郭沫若不仅为影片题写了片名,还题诗两首并在片头亲自朗诵,其中“沥血唤回春满地,天南海北吐芳华”一句,高度赞扬了梅兰芳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巡演的壮举。
早在1937年,26岁的张庚就撰写了《梅兰芳论》一文。当时他主要从事话剧运动,且受鲁迅影响,曾认为“梅兰芳的艺术是纯粹的封建艺术”。1949年,两人一同参加了第一届文代会;1954年,梅兰芳与张庚分别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正、副院长;1957年《戏曲研究》创刊,二人同为编委;1959年7月1日,张庚与马少波作为入党介绍人,见证了梅兰芳的入党宣誓仪式;196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并入中国戏曲学院后,梅兰芳与张庚仍分任正、副院长。工作上的紧密联系,为张庚深入了解、重新评判梅兰芳提供了契机。他先后撰写8篇以梅兰芳为主题的文章,全面总结其艺术成就,盛赞其为“一代宗师”,并指出梅兰芳注重表演的“适度感”与“内在的节奏”,最终形成了“温柔敦厚、雍容华贵”的独特艺术风格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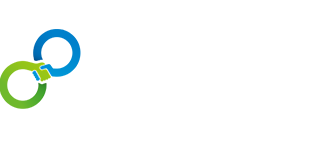
 2025-06-29 07:58:20
2025-06-29 07:58:20 浏览次数: 次
浏览次数: 次 返回列表
返回列表 友情链接:
友情链接:





